公益中的性别意识 | 交流·反思·发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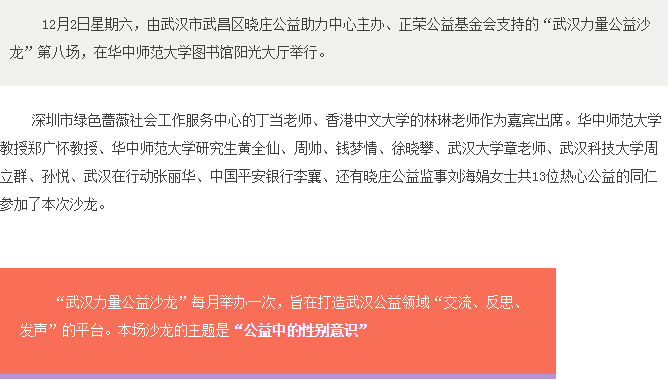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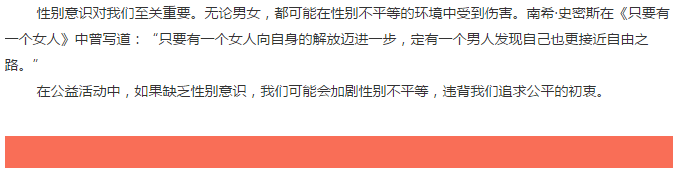
丁当:
刚刚我已经介绍了,其实我的正名叫丁丽,但是我后来在工厂上班,说话特别多,车间工友们就觉得我很叽叽喳喳的,于是叫我丁当。所以丁当这个名字就这样延续下来。
我们今天所有的话题跟性别有关系。
我刚刚简单记录了一下大家的名字,其实从性别的角度看,从出生就有性别了。从你出生起名字的时候,家人对你的期待就不一样。比如“海娟”,娟是女字旁的,还有“丁丽”、“梦婷”,这些都是很女生的名字;而比如男生“大雄”起名就是“雄”,对他的期待是一个很男性的期待。从性别角度来说,名字是个很重要的载体,贯穿你出生到你整个教育的背后。
从起名字开始,父母对我们就开始男生女生区别对待。如果你生来是个女生,就希望你是美丽的、文静的,那我们教育女孩子就要会做家务啊、淑女啊、长得漂亮啊;但是是男孩子的话,你可以调皮捣乱,你要学着胆子大,摔倒了不要哭。所以从你出生开始性别期待就不一样。
一想到女性,就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是“身体消费”。像刚才大家提的“高跟鞋、烈焰红唇、很漂亮”这种,它是一种消费的概念,无论在大街(海报、公交站台等)上,还是电视上,它是把女性当做一种展示的、被观看的“花瓶”,让女性作为一个被观赏的存在。但是谁在观赏呢?主要是男性。有些女性就会想:“我要怎么样去满足男性的要求?”身体消费就一定会对身体进行评判,比如说女性一定要有身材,然后有些女生就说要减肥,有些女生就说要长得够漂亮,会化妆。
第二个关键词是“照顾者”。一想到女性,一般以什么职业为主?幼师、护士、服务员、家政工……男性的角色一般是什么?设计师、工程师、老板、领导等。很多时候男性是掌握更大的权力跟资源的。而不管是公领域还是私领域里面,你会发现女性在职业方面或者家庭里面她更多是一个照顾者的角色。小的时候照顾弟弟、妹妹、家庭,长大嫁人要做家务、照顾小孩、照顾公公婆婆,照顾另外一个家庭。在公共领域的时候,她可能会照顾病人(做护士)、照顾小孩(做幼师),还有做环卫工、服务员(服务员还会被消费,需要长得够漂亮)。所有权力的掌握者、法律的制定者,都是以男性为主。而作为“照顾者”,女性在大环境里面很难变成一个主要领导人。这是整个父权制度及社会对女性的双重压力。
我们会把性别分为两种。一种是生理性别,这是天生的,比如女人生孩子,来月经,男性有喉结,生殖器也不一样,这基本是不可变的;一种是社会性别,这是后天形成的,这是社会赋予的,比如女生一定要够漂亮,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反过来?男性可不可以做护士?男性可不可以做家务?女性可不可以做工程师?女性可不可以变成一个领导人?
我们说的产假,半年的产假你觉得好还是不好?社会似乎试图在制度上去保障女性的权益,但半年产假会让单位觉得女生很麻烦,这对女性的应聘是很不利的。我们的产假如果换过来,三个月是男性,三个月是女性。那么她就业的时候用人单位也不会觉得说我只要男性不要女性。
产假实际是强化了女性“照顾者”的身份,会把你的范围缩得更小。如果你是八小时上班,你还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产假期间你24小时都是工作的状态,照顾小孩是个很辛苦的工作,还要做家务劳动。所以从制度层面看,我个人觉得产假应该给男性多分一点,让男性有更多机会去承担照顾者的角色,让他去体验当爸爸的这种角色,并不是把所有的事情都甩给女性。所有的假期都应是有这样的考虑。
从工作的角度看,我们在一线做一个活动,往往参与活动的也是男性居多。我们发现很多时候男性的表现欲望比女性更强,这是从小的成长系统里面,他会很自然地觉得我要表现自己,我要有自己的主张;女孩子有什么观点,一被打压几句她就难再说了。这是成长环境的问题。怎么应对这些问题呢?所以我们很多工作里边会有性别的敏感度,就是在场会给女性多一些机会。还有,你要让她感觉是安全的,安全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女性是很没有安全感的。我从一个最基层的角度出发,在农村里面女性是没有地的,她嫁过去也没有地,就是她是没有根的,没有家没办法扎根下来。男性的话,最起码传下来的房子是他的,地也是他的。
最后我再说一下我们机构的工作吧。我现在做女工服务也有七八年,我们机构倡导的口号叫“女工自主,蔷薇绽放”。为什么我们机构叫绿色蔷薇?绿色就是有希望、有生命力,蔷薇是玫瑰的一种。每年的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会讲一个口号,就是“面包与玫瑰”,面包代表着生存保障,玫瑰代表着生活质量(体面劳动)。我们希望所有的女工有个好的生活质量,有体面的劳动,就是我们都尊重公领域和私领域的劳动价值。我们希望让更多女工可以自主发声,自主表达!
谢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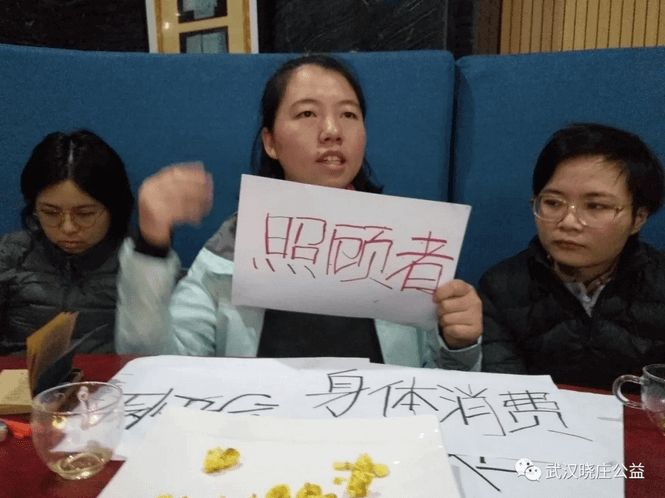
林琳:
我们这一路骑行过来,不仅充满着劳动的元素,也充满着性别的元素。
在绍兴,我们去了秋瑾纪念馆,也去了鲁迅纪念馆。我们看到,女性在整个历史,具体到社会运动的历史中,她们的角色也是被淡化的。鲁迅纪念馆是人头涌动的,但是秋瑾纪念馆是冷冷清清的。在鲁迅纪念馆里面,有说到鲁迅跟许广平的一些爱情故事,而许广平在这些历史的论述当中也只是一个陪衬者。纪念馆里面还有专门展出一套许广平给鲁迅绣的枕套,就是像刚刚丁当所说的,强化着“照顾者”这样一个角色。
在富士康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点就是体检。有一个内科体验,体检的时候十几个人排队,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你要躺在那个床上,医生把你的衣服掀开摸你的肚子,但是完全不管后面那一排人有男有女。这样是基本没有什么隐私权的。
针对我们这一路的这些元素,我就说几个点吧。
第一点,我自己的工作是在做一个职业学校学生的项目,里面也是非常强调劳动平等的意识和性别平等的意识。我觉得第一点是,如果我们以后出来做服务,想做一些性别相关的教育的话,其实生殖健康教育和性别教育是密不可分的,不要以为做生殖健康教育就只讲生理知识。
举个例子:怎么选择内裤?如果你是做生殖教育的话,你可能说我们选内裤要宽松、棉质。但是你要考虑到这个社会有些对女性的消费主义,别人可能会说那些是大妈内裤,包括维密推崇的也是蕾丝的、丁字裤、紧身裤,所以说生殖健康教育和性别平等的教育是不可分割的。
第二点是不要脱离阶级去谈性别。因为在我们这个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体系里面,它就是一种按性别去分工。像我们接触的职校学生,很多女生初中的时候数学本来很好,不知道为什么到了高中就突然倒退,老师也跟你说女生是学不好理科的。然后包括现在很多BAT里的程序员都是男性,主导的还是一个性别的分工。当女性被分工到服务行业的时候,她付出的很多都是情感劳动,这些情感劳动往往都是无形的,所以会被忽略。
我们国家现在在谈工匠精神,谈工匠精神一般也是更多地谈男性的形象,而没有去强调女性在工业生产中的地位。女性在工业生产中是没有地位的,她们只是默默在服务业里去付出她们的情感劳动。
第三点是比较紧迫的一点,我之前也在“土逗公社”里写文章,我们有一期是关于丁璇的女德班,就是去挖丁璇后面的产业链。其实丁璇后面是一个河北传统文化研究院,他们搞了很多女德班、养生班去营利。所以要警惕性别偏见与资本的勾结。政府不监管,市场也不淘汰这种性别倒退的活动,那我们个人应该怎么面对这些大倒退呢?每个人其实都应该参与进来,去进行自己的反抗!我自己的话,我很希望看到更多女性有一个对自己身体经验的写作,包括我们是怎么经历经痛啊,你去妇科体检你是怎样的经历,只有我们更多地去写作去表达这些经验的时候,这些经验才会被重视,而不是像我们一路遇到很多女工会说“都习惯了”。这种习惯,一方面她们确实很能忍耐,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有些事情是不能习惯了的,要在话语上把它们重新提炼出来,重新强调出来。
谢谢。

郑广怀:
我是个老师,作为老师当然包括在学校里教和不在学校里教两种形式。那么我觉得我如果要去推动人们更多去了解和关注社会性别问题的话,作为老师来讲,第一是在所有的课程里面去加入一些性别的元素,第二是应该有些专门的内容是来讲女性主义、女权主义。
事实上我以前研究更多的是工伤领域,然后我会发现女工工伤有些特别的境遇是男工工伤不会遇到的,比如说你刚好是怀孕期间受了工伤,那就是很麻烦的事情。还有就是受了工伤以后,虽然按照全世界和中国的数据来说,受工伤是男性居多,到达6:1甚至7:1,但是受工伤本身带来的社会后果和家庭后果是女性在承担,我是从这个里面开始慢慢关注到一些关于女工的问题。我去年在给社工上课的时候也会在社工理论里面专门去讲“女性社会工作”,但是我更希望有像丁当这样的或者有些专门做女性主义研究的人来讲这些。
黄全仙:
我想的是关于“女佣”,因为现在家政服务人员有些是兼职的,有些是全职的,很多基本都会住在雇主的家里。她们服务的时间的话基本都是全天,我希望在法律制定的时候,有一个可以保护家政服务人员的条例,让她们有自己的假期,有自己上班规定的时间,而不用全都是在雇主的家里一直保持工作状态。
周帅:
我写了两个词,一个是“倡导者”,一个是“发声”,因为我实在想不清楚自己以后会成为一个什么社会角色,所以倡导者可能更符合一些,社会学的一个使命就是要倡导社会变得更加平等更加和谐。
“发声”,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字面上的,以文字的方式发声;第二个发声是我们去接触他们,是一种接触式的发声,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自己的性别角色,提升自己的性别意识。
徐晓攀:
“调查员”,我是这样一个角色。我现在在农村里面做社会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我意识到一个问题,我们调查的工具比如那些问卷,我们没有考虑性别的差异,或者说没有考虑性别平等的问题,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不自觉地就把女性排除之外了。我们调查的是户主,但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户主一般是由男性承担的,我们在了解信息的时候是很少能了解到女性的态度和观感。我现在在操作中间可能会有意识地偏向于多调查一些女性。
丁当:
我们是一个女工服务机构,我也是机构的负责人,所以以后会继续做女工服务来推动。很多人好像会代表女工,比如媒体,所以有时候是拿相机的人比工人的话语权更多,权力关系就开始不对等了。其实,实际最能够说清楚这些问题的人是他们自己。关键是得有安全的环境,让他们愿意去表达一些东西。
章云萍:
我是一个教师,我最开始来到丁当的机构就因为很关注性别的议题,所以毋庸置疑我在我日常生活中和上课内容当中都会去贯彻这个性别的视角。当然我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别人,即使我觉得有些东西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情理上都是说得通的。不止是上课,生活当中各个方面我都会用性别视角去看待问题,去影响更多的人。
钱梦情:
我现在身份是一个学生,我将来可能会当老师。如果谈到性别,我刚刚谈到过红黄蓝幼儿园事件,有些媒体可能过分夸大,把重点关注在受伤的群体身上,但是我觉得幼师作为一个群体其实也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对老师这个群体应该“去污名化”,特别是女幼师,而且幼师群体一般是女性,其实也是对女性的一种污名化。
刘海娟:
近期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无业,我写的角色就是“妈妈”,这是我比较长的职业,也是一辈子的职业。我的孩子还是个男孩子,日常生活里可能并没有更深入一点的跟性别意识相关的教导,我下一步会给他讲一些性别意识的绘本,还有就是生理知识。
我发现周边小区里如果是女孩的话,母亲一般都具备教给女孩子自我保护的意识,但是反而男孩不太在意对他的性别教育,顶多是告诉他一下你不能欺负女孩子,不会告诉他和女孩子的区别这些。所以我下一步可能会身体力行地做一些性别意识的教育。
林琳:
我写的是身份是“学者”,虽然我也不寄希望于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学者看上去好像是个冷冰冰的词,但是加个“女”字在前面的话,就变成“女学者”,其实女学者是有很多压迫在她们身上。虽然大家开女博士的玩笑开得很开心,但是其实女生是非常辛苦的。在整个知识生产体系里面,女性的地位也是处于边缘的,我们也知道,像我们学社会学,马克思、韦伯这些都是男性,女性的学者在她们的文章发表、文章被引用等方面也是很边缘化的。
我提出来一个方法是一个很小的点,就是我们在做学术论文引用的时候,可以多去引用女性学者的观点,这是很实在的。如果我们能多引用一些女性学者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抱团取暖。

